《南楼旧东风》是带刀侍卫的猫创作的一部古代言情小说。故事围绕着云娘小莲展开,揭示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不可思议的冒险经历。这部小说既扣人心弦又充满惊喜,令读者难以忘怀。笔尖悬在雪白的宣纸上方,迟迟无法落下,一滴饱胀的浓墨终于承受不住,“嗒”地一声,…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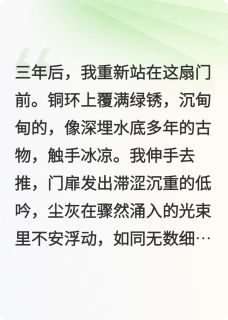
三年后,我重新站在这扇门前。铜环上覆满绿锈,沉甸甸的,像深埋水底多年的古物,
触手冰凉。我伸手去推,门扉发出滞涩沉重的低吟,尘灰在骤然涌入的光束里不安浮动,
如同无数细小的灵魂在无声起舞。屋内昏暗,一股陈年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,
混杂着若有似无的药味。然而,视线越过弥漫的尘埃,
我的目光被牢牢钉在屋子深处——那架锦瑟,静默地横陈在蒙尘的旧床上,
像一艘被遗弃在滩涂上的孤舟。凤尾弦松松垮垮地垂落,一如主人离去时疲惫的姿态。
这正是她昔日习惯摆放的样子,一丝不乱。指尖抚上冰凉的弦,一股寒意直透骨髓。
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她指尖的温度和隐隐泪痕。恍惚间,
耳畔又响起她幽幽的叹息:“我若走了,弦便让它这样松着罢……”声音轻得像柳絮,
却重重砸在我心上。那时,我沈砚,在这繁华帝京中,是沈尚书家最惹眼的公子。府邸巍峨,
出入随从如云,挥金似土。而云娘,她是南楼那重重翠箔华灯深处,
一曲清歌便能涤荡喧嚣尘土的所在。记忆里最鲜明的一夜,翠箔低垂,光影迷离。
她抱琴而坐,纤指在弦上拂过,泠泠之音如碎玉滚落。我已有七分醉意,
枕在她单薄却温软的肩上,鼻息间盈满她身上清雅的幽香。她微侧着头,低声吟唱,
温热的吐息若有似无拂过我的耳廓,每一个字都像带着钩子,钻进我的心里。“公子,
”一曲终了,她微微侧首,眼波流转,清亮的眸光在灯影下闪烁,“今日这曲子,可还入耳?
”我并未答话,只将她往怀里拥得更紧了些。彼时年少轻狂,只觉满城灯火,
皆可为我掌中长明。父亲每每痛斥,责我耽溺声色,辱没门庭,我不过一笑置之,
依然每日策马扬鞭,穿过飘飞的柳絮,马蹄踏碎一地残春——只为快些抵达南楼,
快些见到她。然而家族的***终至。那日回府,父亲面沉似水,立于厅中,
脚下赫然散落着几封密信。他枯瘦的手指因狂怒而剧烈颤抖,直直指向我:“沈家百年清誉,
簪缨世族,岂容你如此糟践!为一个**歌伎!”我欲辩,却觉喉头哽塞,
所有言语在父亲***般的怒火下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最终,
我被两个孔武有力的家仆强押上北去的马车。隔着车窗,纷飞如雪的柳絮迷蒙了视线,
我拼命回头,在道路的尽头,一个素白的身影孤零零地立着。风卷起她的裙裾,
像一只挣扎欲飞的白蝶。她抬手掩唇,一声压抑的呛咳从指缝间溢出,瞬间被喧嚣的风吞没。
柳絮扑上她单薄的肩头,她只是那样站着,定定地望着马车远去的方向,
直到成为一个模糊的白点,最终消失在视野的尽头。自此,关山万里,音书断绝。三年羁旅,
终得南归。马匹刚踏入熟悉的街巷,我甚至来不及掸去一身仆仆风尘,便勒转马头,
直奔铜驼街深处而去。心早已飞向那低矮的门庭,飞向那个魂牵梦萦的身影。
茶肆的掌柜是旧识,一见我翻身下马,便慌忙从油腻的柜台后绕出,脸上堆着笑,
眼底却藏着难以言说的踌躇和怜悯。“沈公子?您……您这是来寻云姑娘?”他***手,
声音干涩。我喉头发紧,心悬到了嗓子眼:“云娘……她可还好?
”掌柜重重地、长长地叹息一声,摇着头,声音压得极低:“公子……您……来迟一步了。
云姑娘她……去年春上一场急症,来得凶险……没熬过去……人,已经没了。
”“没了”二字,如同两柄烧红的铁锥,狠狠凿穿了我的头颅。刹那之间,
市井所有的喧嚣——叫卖声、车马声、孩童的嬉闹声——瞬间被抽离,
只剩下一种尖锐的、持续不断的白噪在颅腔内疯狂嗡鸣。脚下虚浮,我踉跄一步,
全靠手死死撑住那油腻冰冷的柜台才勉强没有倒下。春天……又是柳絮纷飞的春天?
她掩唇那一声轻咳,竟是命运早早投下的、残酷无比的谶语?“……她……葬在何处?
”喉咙里像是堵满了滚烫的沙砾,每一个字都磨得生疼。掌柜的头垂得更低,
声音细若蚊蚋:“公子……她一个无根无基的孤女……哪有什么正经坟茔?
病中……连个端汤递水的人都没有,
后事……后事也草草了结……听说……连件像样的妆裹也……”他顿了顿,
似乎不忍再说下去,却又想起什么,“倒是听她隔壁的吴婆婆提过一嘴,
说她病得昏沉糊涂时,手里死死攥着个小小的蓝布包,怎么掰也掰不开,
嘴里只含混念着什么……像是……‘画’?”蓝布包?画?我的心猛地一缩。
失魂落魄地辞了掌柜,浑浑噩噩回到沈府。宅邸依旧深广威严,红墙碧瓦在暮色中沉默着,
却只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上来,冷彻骨髓。入夜,更深露重,我披衣枯坐,毫无睡意。
那“蓝布包”三个字如同鬼魅,在心头缠绕不去。终于,我起身,几乎是粗暴地翻箱倒柜,
终于在书房角落一个落满灰尘的旧书箱最底层,
指尖触到了一个硬硬的、被布紧紧包裹着的卷轴。解开那褪色的蓝布,指尖抑制不住地颤抖。
丝绦滑落,卷轴徐徐展开——是她!画中云娘,眉眼如初,正倚着朱栏,唇边笑意清浅温婉。
画师技艺精湛入微,竟连她眼中映照的南楼点点灯火,都细细描摹了出来,那眸光深处,
仿佛蕴着千言万语。目光急切地移向题款处,一行娟秀小字刺入眼帘:“崔徽遗容,
留待君归。”崔徽!那个为情人留像而逝的唐代女子!她竟以此自比!
一股巨大的悲恸混合着难以言喻的恐慌瞬间攫住了我。她那时……便已预知了自己的结局?
这画,是她病骨支离时,如何挣扎着为我留下的最后念想?那个蓝布包……她攥着的,
就是它吗?她是以怎样的力气,在生命的尽头,死死护着这份留给我的微光?“孽障!
”一声暴喝如同惊雷在死寂的书房里炸响!父亲不知何时已立于门口,面色铁青,
眼中燃烧着狂怒的火焰,须发皆张。他几步抢上前来,枯瘦如鹰爪般的手带着劲风,
凶狠无比地抓向那画轴!“父亲!”我如同护住稀世珍宝,更如同护住云娘最后一点魂魄,
本能地将画轴死死抱在胸前,声音嘶哑,“这是云娘!她留给我的……”“**东西!
死都死了,还留下这等污秽之物来蛊惑人心!也配玷污我沈家门楣?”父亲怒不可遏,
额角青筋暴跳,枯瘦的手指爆发出惊人的力量,猛地攥住画轴的一端,狠狠向外一扯!
“刺啦——!”那清脆刺耳的裂帛声,如同最锋利的刀,狠狠劈开了凝滞的夜,
也劈开了我最后的防线。薄薄的宣纸如何经得起这般蛮力?
画中云娘含笑的容颜瞬间被从中撕裂!
清亮的眼眸、温婉的唇角、倚栏的纤影……全都碎裂成狰狞的、不成形状的碎片!“不——!
”一声绝望的嘶吼冲破喉咙,我疯了一般扑过去,徒劳地想要拢住那些纷纷扬扬飘落的残骸,
如同想抓住被狂风瞬间吹散的流萤。那些带着她笑容的碎片,如同失去生命的灰白蝶翼,
带着最后的温度,绝望地在我徒劳伸出的指缝间飘零、坠落,散落一地。父亲盛怒之下,
犹不解恨,竟抬脚,带着一种毁灭一切的暴戾,狠狠踏向地上那片最大的残骸——那上面,
恰好残留着云娘温柔凝望的半张脸!沉重的官靴鞋底,带着泥土和阶前的尘埃,重重碾过!
“噗”的一声轻响,像是什么柔软的东西彻底破灭。我僵在原地,伸出的手凝固在半空,
全身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彻底冻结、凝固。地上,
只有几片被肮脏鞋底污迹彻底玷污、揉皱的碎纸,
如同被践踏后碾落尘泥的、零落成泥的花瓣。云娘留在这世间、留给我的最后一点清晰模样,
在我眼前,被我的至亲,以一种最粗暴、最彻底的方式,抹去了。夜,浓稠如墨,
沉重地压在沈府高阔的屋宇上。书房里,一灯如豆,昏黄的光晕勉强撑开一小圈模糊的光明,
灯芯不安地跳跃着,在墙壁上投下巨大而摇曳的阴影。我铺开一张崭新的素白生宣,
墨已研浓,执笔的手却抖得如同风中残烛。闭上眼,用尽全身力气去回想,
去捕捉:她眉梢挑起时那恰到好处的弧度,唇角微弯时那醉人的深浅,
还有眼中映着南楼璀璨灯火时,那一点最最动人的、仿佛盛着整个星河的光亮……然而,
越是用力,那些曾经镌刻在心底、无比清晰的线条,竟在脑海中一点点模糊、扭曲、融化,
如同被雨水无情洇开的墨痕,再也无法聚拢。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,后背冰凉一片。
笔尖悬在雪白的宣纸上方,迟迟无法落下,一滴饱胀的浓墨终于承受不住,“嗒”地一声,
重重坠落纸面,迅速晕染开一个丑陋而空洞的黑斑,像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深渊。
一阵夜风猛地从窗隙灌入,烛火剧烈地一晃,光影在墙壁和纸面上疯狂地扭曲、跳动。
就在这光影剧烈摇曳的刹那,我悚然一惊,
一股冰冷的绝望瞬间攫紧心脏——那案头昏黄跳跃的光晕里,
竟再也无法清晰地拼凑出她完整的、生动的笑容!遗忘的深渊正张开无形的巨口,
贪婪而无声地吞噬着她留在我心底的最后一点痕迹。笔,“啪嗒”一声,从无力的指间滑落,
在素白的宣纸上拖出一道狼狈而绝望的墨痕,歪斜无力,如同垂死的挣扎。灯影兀自摇晃,
映照着徒然四壁。原来人世间最深的永诀,并非黄土相隔,而是记忆深处那抹最珍视的微笑,
被时光残忍地、一痕痕,悄然擦去,最终归于永恒的虚无。几天后,我避开府中所有耳目,
如同一个游魂,再次踏入铜驼街那间弥漫着茶香与市井喧嚣的铺子。
掌柜见我形容枯槁、眼窝深陷,吓了一跳,连忙将我引到后堂僻静处。“公子,
您……”他欲言又止,眼中满是同情。“掌柜的,”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,“烦劳您,
帮我打听个人。云娘……病重时,身边可还有人照料?或者,
可有人知道那幅画……是谁替她画的?”我顿了顿,艰难地补充,
“还有……她最后……葬在何处?哪怕只是草草掩埋,总该有个去处。”掌柜皱着眉,
仔细回想:“照料……唉,那阵子她已病得下不来床,南楼那边……您也知道,人走茶凉。
倒是一直跟着她的那个小丫头,叫……叫小莲的,还算有良心,偷偷跑去看过几次,
送些汤水。后来云姑娘没了,也是那丫头哭着求了街坊几个老妇人,帮着收敛的。
至于葬处……”他摇摇头,叹了口气,“听说是城西乱葬岗那边,具体哪一处,
就真没人说得清了。荒草萋萋的,埋的人又多又乱,难找啊!
”“小莲……”我默念着这个名字,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“这小莲现在何处?
”“她原也是南楼买来的丫头,云姑娘去后,鸨母嫌她晦气,
转手就卖给城西一家染坊做粗使丫头了。日子……想必艰难。”掌柜说着,
从怀里摸索出几个铜钱,“公子若要去寻,那染坊就在城西水井巷最里头,
门口挂着靛蓝布幡的就是。这点钱……您替我捎给那苦命的孩子吧,云姑娘在时,
待我们这些街坊,也是极和气的。”我心头一酸,谢过掌柜,接过那几枚带着体温的铜钱,
转身便往城西奔去。水井巷狭窄潮湿,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染料和污水混合的怪味。
巷子尽头,果然有一家低矮破败的染坊,靛蓝色的布幡在风中无力地飘荡。
一个穿着粗布短打、身形瘦小、脸上手上都染着斑驳蓝靛色的女孩,